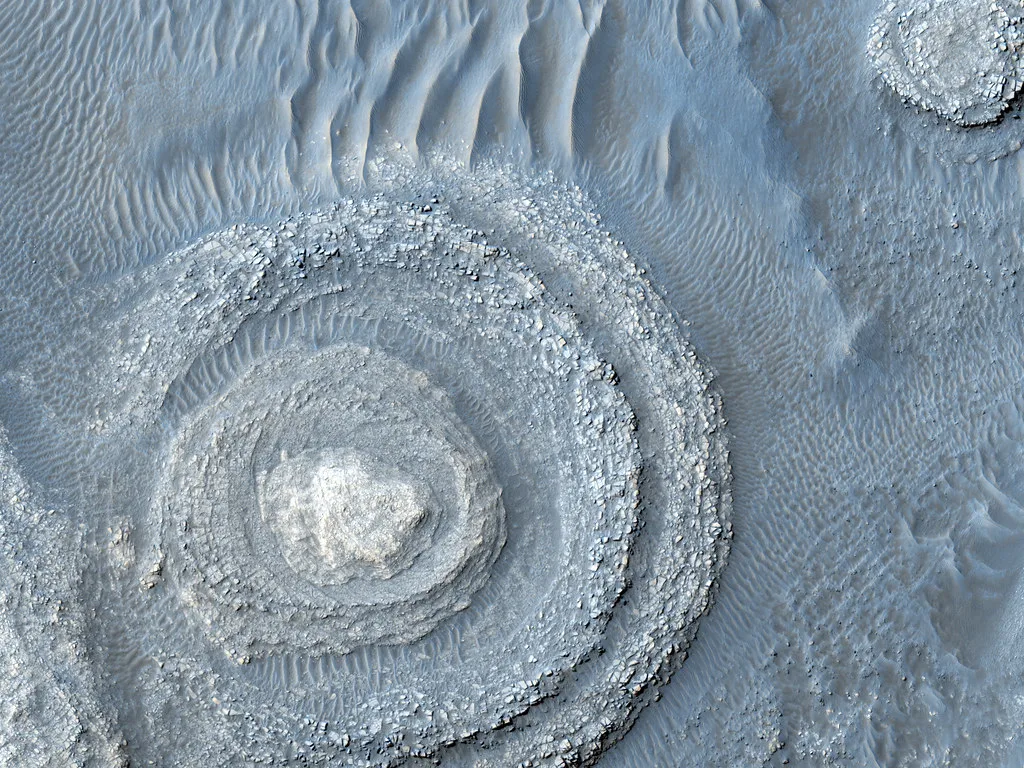2023年没有读完一本完整的书(除了翻译的几本以外)。
几乎所有的书(一共两本)都是在飞机上读的。一本是在来回埃塞的路上阅读《革命-后革命》。另一本也是革命书籍,在国内飞行时阅读的《The Day the Revolution Began》。余兴阅读,或许是那篇讨论反革命的旧文——“词汇量决定论”。
前一本书大致是8月读的,留下了一点笔记,后来因为忙碌,就没有进一步处理。略加修改,姑且抄录在这里,做一个备案。老徐说,这点选题都要够得上开研讨会了。但这一年,因为结识梁俊和大辉的缘故,我的关注重心逐渐向着被教会边缘化的知识分子,或者有意识投靠教会的知识分子偏移,也有意识(或被推动)向着年轻职青偏移。但下面的笔记和思考,也可以说是我对自己这30年信仰经历的顿挫和反抗吧。我提到的事,都是我经验中有底色的……
下面的内容几乎是笔记的抄录,仅隐去了几个可能不适合出现的名字。对于这些问题,我没有认真回应的时间,或者经验还不足以回应。所以就这样吧:
真诚信仰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一方面肩負啓蒙工人階級歷史自覺的任務,一方面因爲自身並非無產階級,又需要向工人階級學習,改造,成爲情感和態度上的無產階級革命者。否則,就是自我毀滅。p50
一個傳福音的知識分子,如何自覺這種認知與信仰的差異,在啓蒙的同時靠向〝基要主義〞,靈恩主義,教條主義或神祕主義?
一個優秀的學者,如何說服自己分裂地接受創造論,年輕地球?爲了永生而放棄的現實,是否有充分補償?
基督徒中产家庭對於子女教育的重視而不得其法,是否是對永生的不滿足?
福音運動缺乏對社會階層的分析,對於〝罪人〞意識與榮辱文化,面子文化的切入不深,沒有明確方法研究,與社會脫節?
一個運動,是個人性質的改变和推动,還是社會性質的改變?
当代社会的“打工人”和雇佣关系,模糊和打破了階級意識,带来的原子化社會,房地產,教育和獨生子女的牽涉,讓社會動員的難度增加。
本質問題:福音對中國社會的意義何在?当〝人民〞的概念更为强调,而階級的概念相對弱化,如何拓展福音。
福音的內核是固定的:基督耶穌的十字架,神的話語和主權……教會的組織與功能結構,權力結構的穩定性與張力。福音的勝利必定是超越宗派的〝基督〞的勝利。釋經學仍然將是唯一合理的聯合要素,達成共識和理解的關鍵。
活潑的講道和寫作至爲關鍵。
起點原本現代的福音運動,被前現代,反理性,反科學的基要主義思潮所浸染,侵奪,失去其對知識分子的吸引力和更新爲煥然一新的感覺,構成對心靈的壓迫和對壓迫感的麻木與承認,從教義理性來壓制情感自發,性別壓迫帶來普遍的不滿,女性受壓感嚴重,而男性愈加迫切地強調壓迫-順服敘事下的性別互補。
接受施瑋的〝叛教者〞,和接受李麗的〝企業家〞同樣艱難。
问题意识:普遍的传福音困难,存量事工的原因是什么?
寻找福音对特定人群的切入点,还是寻找福音对特定人群具体关切和迫切的心理、社会、精神、组织参与(民主生活)、宗教(来世与超越境界)之解决资源。
对福音本源的亚洲性认识。
ciu,一个持续百年的“理想”社区组织。为什么倪柝声组织的小群会内聚化、倪本人无法脱离中国传统士大夫的色情性趣?与其有染的两三位姑娘的心态与文化根源?逼迫叙事下的抵赖与消解。马丽的叙事与施玮的叙事,反应为何如此不同?可以用传统教会与当代城市教会的比较研究来展开分析吗?(方法论问题)
美国经验的平移,对于中国教会的影响:
- 资金和资源投入,奖学金与神学培训资源的开放
- 信息不对称性造成资源无效投入
- 神学地位(传统)不对称性造成城市教会的畸形
- 韩国(鲜族)模式的对标与资源偏倚造成持续性影响(包括..神学院的问题)
- 属灵影响力应该是一种扎根文化的影响力,而不是规模和人数的竞争和比较。
- 下一代焦虑,特别是下一代领袖的焦虑问题
- joshua harris 20岁接班的焦虑;mark drisco;
- …接班人问题
- 异议人士转型牧师的教会理想与治理能力问题;幼稚的政治动员手段(签名)与低水平的逼迫叙事“圈套”
- …的洛桑会议代祷与包装的政治诉求
- 强势文化下神学教育的殖民主义倾向
- 翻译事工的意义与意识形态问题
- 知识分子基督徒的苦恼
- 放弃知识分子批判责任和社会责任的第一代城市基督徒
- 他们的第二代命运与信仰实质如何?
- 这是否表明福音的切入角度有严重的、有待识别、更有待梳理、探索和设计解决方案的问题
- 稳定统一的国家结构,人民意识的潜意识根据,是否使得福音切入的秋雨模式在这个时代阶段必然遭遇挫折,外部的怀疑与内部的不解
- 宣教动员是一种有限的社会动员。实际上,本地化-近文化植堂,几乎变成首先唤起知识分子基督徒与本地基督徒的和解…
- 知识分子基督徒自我认同的丧失与抽离,不得不安放在本来难以稳定和现实自洽的基要主义意识中。
- 在英美成长的台湾和香港基督徒以语言为掩盖植入的异种神学,和韩国教会利用鲜族基督徒可以对照观看。
- 我的嘲讽、冒犯和现实主义,取代无力感与伤感
- 边缘化的民运基督徒,实在无力融入强势文化,却带着相对强势的神学做了宗派殖民主义者。…。
- 我的威敏情节从何而来?
- 教会的泊来:我以为是一个现代化和西方文明的伴随与时髦,却发现是一个阻碍文明和现代性,甚至在科学、文化、人性解放等方面前现代的、傲慢封闭的意识形态实体。在城市新型教会层面🙂,始终没有融入文化和社会,始终被社会所警惕,时常发生冲突,显出隔膜与异样,没有成为一种参与社会构建的力量。
知識分子對教會諸事的批評,學術的着力,是否天然代表教會廣大的感受和靈性、社會性心理,而他們自認爲所代表的神學是否就是歸正?
如果基督還沒有來,而且從心理感觉上,基督似乎也不大会在我的有生之年到來,我如何過一種有意義的,生命仍然充實飽滿的生活,同時有對教會預備與通往天國有實際促進與把握的討論。盼望如何不至於羞愧。
屠龍勇士如何避免自己惡龍化?牧師如何避免成爲名牧?宣教士如何避免成爲雲弟兄(而不是戴繼宗),改革宗如何避免成爲五月花或秋雨?
福音可以安頓身心嗎?如何安頓?
服侍可以保持熱情嗎?飽滿的理想主義(盼望)如何在日復一日的抵悔之中積累
陳映真的〈人間〉發刊詞,〝因爲我們相信,我們希望,我們愛……〞
改良,尤其是福音對人性的改良(重生與成聖),與啓示錄那樣的革命意象,天地變色日月無光,大有不同。革命本質上是人間推動,還是基督再臨所發動,有着末世論意義上的本質區別。但大規模的逃跑避難,或者小規模的成功逃跑被樹立爲屬靈上令人豔羨的得勝,而不是出於人道主義的關懷與施恩,將會引起一種更輕易的出世思潮和不耐心沈着一點一滴改良和傳福音帶動社會和人性改變的心理。
在此意義上,需要更多批評“五月花”,而不涉及安全敏感的要素。
出埃及是神的大行動,是所有神的百姓得救贖,而非迦南基督徒接應之下,埃及教會一小羣人得了救。關於韓國政府,聯合國等的性質認定,人道主義,而非宗教動機。但保護宗教信仰自由是一個人道主義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