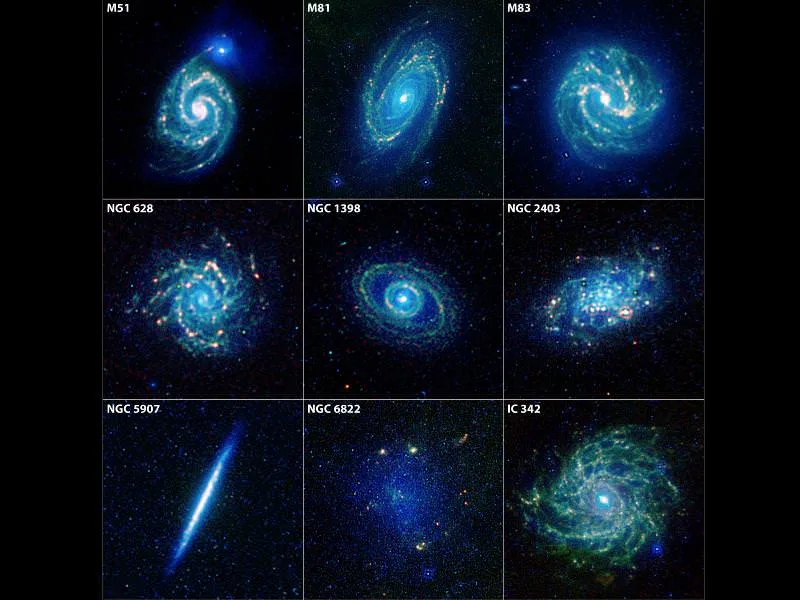最近在听“unbelievable”,辩论很有趣,几乎想要自己开一个中文版的播客了。
这几天在外旅行,顺便阅读N.T.Wright的“The Day The Revolution Began”。
阅读有趣的地方在于,总是可以从好的作家那里得到需要值得反思的问题和方向。Wright讨论了一个重要的神学议题,得救是从“地狱”去“天堂”,还是恢复上帝对人本来的呼召,让新造的人成为新天新地之间有君尊的祭司?
我从前设想的“祭司的国度”针对万国万族成为中保,似乎更在于地上的宽广,而Wright指向天地之间的祭司,一方面在地上宣告十字架的福音,一方面在生活和敬拜中体现出天上的价值观,使得“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也就是说,得救并不是脱离这个悲惨世界,进入天堂,而是恢复与上帝的关系,重新得着呼召,成为使天地和万物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的参与者。
在这个意义上再次反思“润学”的出埃及范式,忍不住又多多感叹一声,觉得其神学上越发虚弱。
朋友问我“didactic theology”和“polemic theology”如何翻译。这似乎真是两个新的术语,他说查询良久,未见于过往的神学翻译。这是两个古老的术语,查尔斯·贺智(Charles Hodge)初出茅庐,在普林斯顿的教职曾经是Professor of Oriental and Biblical Literature, 主攻旧约。不过他老人家后来转攻新约,渐渐成为全科老专家,serving as Professor of Exegetical and Didactic Theology from 1840 to 1854. From 1854 until his death in 1878, he served as Professor of Exegetical, Didactic, and Polemic Theology.
那时已经晚上10点过,我正在上海陌生的地铁站旅行,手机也没电了。于是简单推想了一下语境,给出了一个建议:
教导神学(didactic theology, 即系统神学),论战神学(polemic theology,即护教神学)。
实际上,后来我查到芬尼的1840年神学讲义里给出了这两个术语的解释:
3. Theology is again subdivided into Didactic, Polemic, and Pastoral.
DIDACTIC, is the system of theological doctrines with their evidences, both of Natural and Revealed Religion.
POLEMIC, is controversial. It relates to the disputed doctrines of Theology.
It consists in the controversial maintaining of them, in opposition to their opponents.
PASTORAL, relates to the relations,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Pastors. It consists in a judicious application of the great principles of the government of God to the Pastoral relation and office.
看起来,我的理解大体是对的。不过当代神学门类已经变成”系统、历史、护教、实践、公共、教义、崇拜”之类,确实和200年前大为不同。
和几个朋友聊了6个小时(4-10点),意犹未尽。不过在见面以先,名字和样子是对不上号的,所以算是“网友见面”。好吧,见面的是“圣经女性观的形成”的两位译者,以及另外两位与翻译出版有关的朋友。
有一个朋友的教会要打算“建制”了,真替他担心。神学的收窄,会众的流失,堂会主权的部分或全部丧失(虽然不能说丧权RG),以及运行成本增加,风险增加,大约是建制最大的效果。可以参见从前对建制的讨(fa)论(xie)。
聊了许多有趣的问题,不能一一说清,但获得许多有趣的启发。再次想起三年前可以自由旅行的时间,一年之中偶尔去北上广深之类拜访滞留在一线城市(而非一线教会)的各路“神龟”“大咖”,聊天总是会带来一种智力上的愉悦和八卦上的满足_当然,满足之后还要回到我那二线城市去继续搬砖。听到一个教会鼓励一对夫妻将孕期筛查出严重疾病的孩子生下,后来又轻易地筹得一笔over1M巨款可以将孩子送去美国手术,最后可以说“她在这世上快快乐乐生活了7年”的故事,固然五味杂陈的感恩,但心中的感叹更多是偏安一隅的我,今次来访其实是为着一个一年只需54K的战略项目的筹款而发愁。
最近重拾我的人工智能,希望可以帮助一个预防近视的科研小组做出一点实际能用的工具——据说,中国孩子到了18岁,近视率达到90,这样的族群似乎是前所未有,世之阙如,足以称为广义上近视“已得之民”,简称“已得之民”,需要大力宣唱“Be Thou My Vision”。对比之下,美国孩子的18岁近视率近年大幅提升,也才20,而宝岛孩子的近视率在预防措施之下,近年以0.5的速率下降,正在脱离东亚卷卷圈。
先是,一个多年不见的学生偶然来重庆出差,向华就和他一起来见我。言谈之中向华(他们点的牛排,而我点的蔬菜萨拉)说,在我退出IT江湖这10多年里,他一直在读博、做信息化项目、实施信息化改造,所见之人,似乎也很少有对人工智能领域把握胜过张老师这位“吉祥物”的。我就笑他是同样的偏安一隅,不思进取。而所谓的“吉祥物”效应,可能不过是长期自建博客服务器所带来的信息差而已。
过了几日,Eric来咨询近视筛查建模的问题,说是找了一家软件公司,但沟通不畅,明言在数学建模上搞不懂也搞不定云云。在为了送别Caroline的“不吃小龙虾”桌上浏览一篇据以建模的SCI文章之后,不禁莞尔一笑,对Eric说,这篇文章的模型公式肯定是错的,只是我不知道错在何处。后来和几位顶尖眼科专家、医学统计博士交流,仔细看了一下模型公式和说明,似乎在一个简单的多元回归分析上把交叉项写成了一次项——一个简单而愚蠢的错误。但大概SCI的审稿人也是眼科专家,在数理统计上没有在意,对于公式的验证也潦草,换了我,犯这种错误的文章一定是拒稿了。
但我仍然是一个吉祥物的角色吧,存在的意义在于安抚实际的开发和编程人员,知道有一位退隐10多年的隐秘高手兜底,一切皆有可能。至于具体的工具,大概我是早已经不会了。
阅读似乎有两种。一种是为了证实自己的观念和成见,进一步强化立场的证实性阅读,另一种是为了拓展而进行的探索性阅读。
我以为,阅读信条、信纲、要理问答、要义与敬虔生活指南,大抵是证实性阅读。而我一旦知道自己的立场,就不太愿意花费时间在这样的书籍上,或者说,我的“归正”进路不是从外而内的“建制性归正”。除了自己翻译的这些书以外,我偶尔的阅读大概都是探索性的。我更愿意在探索过程中重整自己的观念,安排那些思而不学的怠慢。
我喜欢一个名叫费马的人,他不是费拉。有一天,费马在阅读一本《算数》时开玩笑地在页边写了一句话:将一个立方数分成两个立方数之和,或一个四次幂分成两个四次幂之和,或者一般地将一个高于二次的幂分成两个同次幂之和,这是不可能的。关于此,我确信我发现一种美妙的证法,可惜这里的空白处太小,写不下。然后,他就再也没有提过这事,直到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