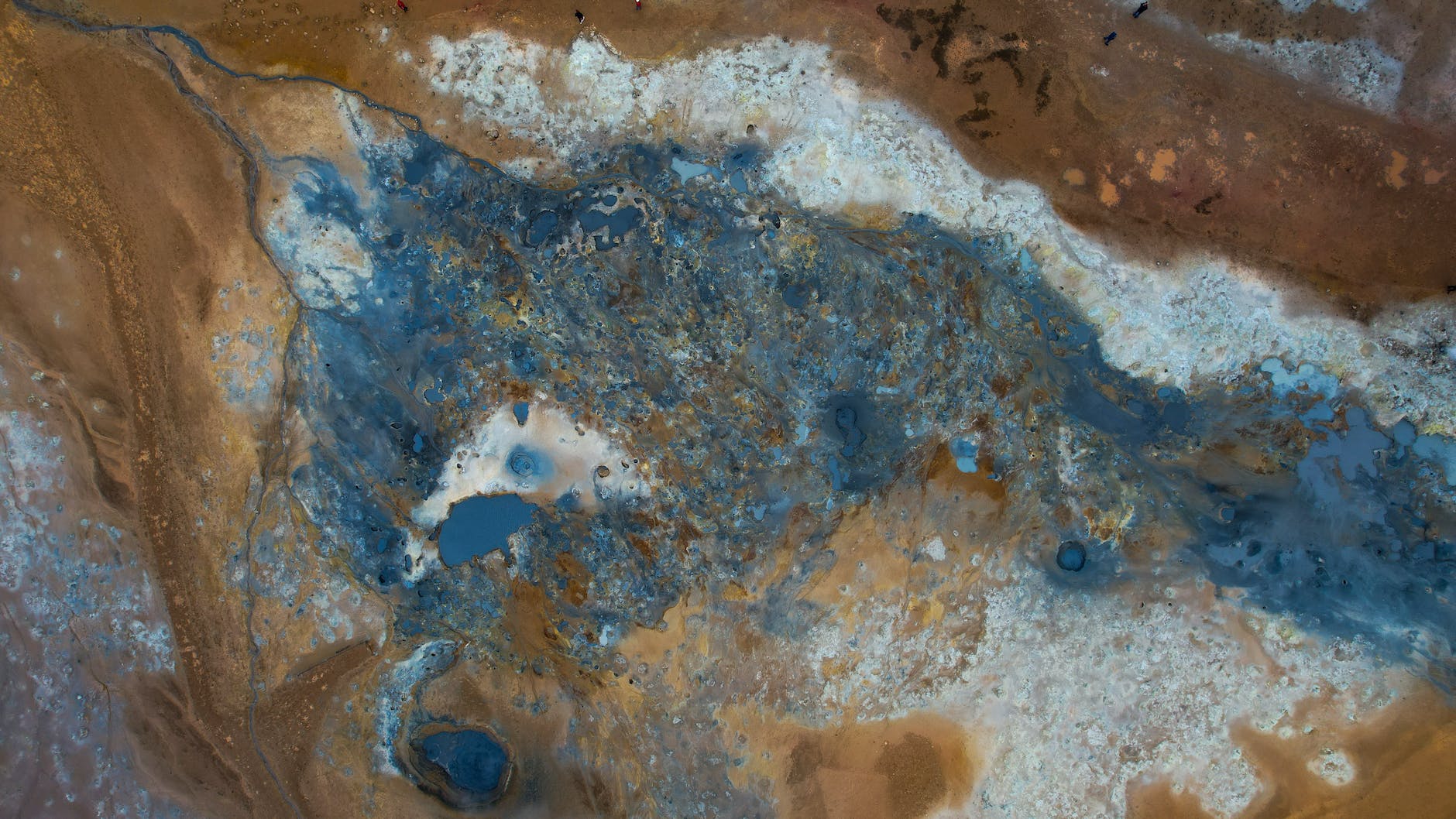疫情之中,闲来无事。这个月开始整理旧债,一一归还。
完成了大部头的《以弗所书释经注释》,补译了《彼得前书注释》,和研经工具定下了下一本圣经注释的翻译意向,Leon Morris的《约翰福音注释》。Morris的《约翰福音注释》,霍纳的《以弗所书注释》,连同前年翻译的F.F.Burce《使徒行传注释》,都是新教神学家的顶尖注释作品。从2015年神学院毕业开始,每年翻译一本重要圣经注释书的工作还能继续坚持下去,也算是目前想来有些价值的事工了。若是这一代人被按下暂停键,至少可以为下一代积累一点工具书。在可以预计的将来,我还看不到汉语神学家们有能力出版自己的WBC或NICOT/NICNT,更不用说NIGTC这样的系列了。在这个意义上,优秀圣经注释的翻译应该是自觉地成为我的优先项目,更何况“研经工具”网站将所有的圣经注释全部免费上网,和那些较为昂贵难得的纸版圣经注释书相比,还是有自己的优势。
NIGTC的主编是Todd Still博士。出于偶然,这个月也在校对他写的《Thinking through Paul》,预备明年为某个神学班开设一门“保罗书信”课程。所有这一类课程,最为缺乏的无疑是教材。市面上关于保罗书信的讨论和注释,或耿于过详,或失之过简,翻译一本篇幅适中的教材虽然无法留名青史,倒也不算浪费时间。
国庆至今,几乎封闭在小区。闲暇之时也完成了《广西宣教史》的校对和补译,以及《主,求你教导我们如何祷告》讲道集的校对。前者已经付印,后者大概很快可以在几个在线书城上线。
陶陶为CIU教育学院翻译的《Distinctively Christian: A Christ-centered Approach to Early Childhood Spiritual Development》也在这几天校对完,交付使用。这个系列还有两本,一本叫做《Distinctively Christian: A Christ-centered Approach to Early Childhood Philosophy & Principles》,另一本叫做《Distinctively Christian: A Christ-centered Approach to Early Childhood Teaching & Learning》,如果可能,都想翻译为中文。看起来,即使义务教育阶段遇到困难,幼儿教育阶段至少还有可为。
处理完这些杂事,这几天发现小区高风险了。所以从今天开始,安心修订《赐予生命的领导力》一书。这是拖延了太久的项目,我的“领导力工作坊”也因缺乏教材而延期了至少1年。这书也是陶陶翻译的,看起来能够长期合作的译者不多,儿子算得上一个。
疫情初起,小区渐渐封闭,我对陶陶说,安心下来,封闭期间工作效率大概会下降一半。他不置可否,大概是不信的。过了半月,陶陶来电话说11.11更新的设备,但工作效率确实下降了许多。他现在实证老父亲说的还是有道理,于是问我这是什么心理现象:“我起初以为,即使不封控,我也不大出门。对我的影响不至于那么大……”
当然,这似乎就是常识而已,一个敏感的人对于失去自由的心理消耗是巨大的,甚至足以影响工作效率。我的工作效率也大受影响,虽然按照日常,我们家本来就采用在家教育,并没有因为孩子们需要回家上网课而打乱节奏。看起来,像我这样自律而节制的译者都会觉得翻译为难,今年的GDP目标实现起来还需要统计局更努力才行。
总结起来,封控期间洗碗的频率下降了30%,所以可以利用洗碗的时间刷完了权游——没有采用倍速。正好在翻译《领导力》,看起来龙妈前期的领导力值确实是0,所谓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放松的时候,带着Angela在院子里游戏,我在手机上看《现代性的神学起源》或者《新政治科学》。
微信上《新政治科学》第5章的试读,《诺斯替(灵知)革命:清教徒的案例 | 沃格林》,感谢老徐的朋友圈指引。沃格林的讲座是1950年代出的,这本书也被圈内公认为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学著作之一。我有些疑惑,自己竟然错过了,从前没有读过。仔细想想,虽然我基本上只读英文原著,但选择读什么书,仍然依靠中文翻译出版市场。
对我早期世界观造成影响的以赛亚柏林,哈耶克,卡尔波普,弗里曼,阿兰雷蒙之类(大部分是犹太人),无不是因为翻译引介而来。倒是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对哲学的关注很少,以后也没有什么时间再阅读哲学类图书,精力都放在见效快的教牧类书籍上去了。
不过疫情期间,生活停顿,所谓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固有读哲学的心情。对于日下在教会神学中占据主流的改革宗思想而言,沃格林对灵知主义的政治学批判是很重要的进路,帮助我整理自己零零散散的神学观察和反思。《现代性的神学起源》帮助我看到人本主义与宗教改革进路在回答某些核心问题上的失败,如何引发了现代性进程;《新政治科学》帮助我看到清教徒神学在文化上的断裂,反过来理解“灵知主义-马列主义-中国革命”到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文化断裂,梳理我对某些神学“代表”出于本能的沟通不力,或者对于济州岛普利茅斯的鄙夷。
读了一点沃格林的原文,比较了《新政治科学》的两个中译本。我倒是觉得段保良的译本是不错的,与后面孙嘉琪(李晋校)的译本各有好处。在我比较的第5章第1自然段:
对灵知主义经验的分析所得出的现代性概念,其含义似乎与 这个词的传统含义不相符。西方历史通常以1500年为正式分界, 其后为西方社会的现代阶段。然而,如果现代性被界定为灵知主义的生长,这种生长大约早在9世纪就已开始,那么,现代性就是西方社会内部的一个过程,深深地渗透进了中世纪时期。因此,前后相继的分期概念,应该由连续演化的概念来取代,在这个演化过程中现代灵知主义成功地崛起,压倒了一个源于地中海世界对人类学真理和救赎论真理的发现的文明。这种新的概念本身不过是反映了经验主义史学的当前状况,所以无需进一步证明。然而还有一个问题是,传统的历史分期是否和灵知主义的问题毫不相关; 如果一个符号在西方社会的自我解释中被广泛地接受,却与对真理的代表这个根本问题毫无联系,这本身确实就是奇怪的。
——段保良
我们针对诺斯替经验的分析,已经导出了一种现代性概念,它似乎与这一术语的传统含义有些差异。在传统上,人们以公元1500年左右作为正式的分界点,将西方历史划分为几个时期,1500年之后的时期是西方社会的现代阶段。然而,如果现代性被界定为诺斯替主义的增长,这可能早在9世纪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那么它就变成了西方社会内部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深入延伸到了中世纪时期。因此,连续性阶段的概念就会不得不被一种持续演变的概念所替代,在其中,现代诺斯替主义成功兴起,进而取得了对一个源自地中海地区,发现了人论和救赎论真理的文明传统的支配地位。这一新的概念本质上不过是反映了经验性历史编撰学的现状,因此,我们就无需进一步的证明了。但是,这里仍待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传统的历史分期与诺斯替主义的问题是否没有任何关联;因为,如果一个符号在西方社会的自我解释中已经获得了如此广泛的接受,却与真理代表的基本问题之间不存在某些方面的关联,这的确会令人感到惊讶。
——孙嘉琪
THE analysis of Gnostic experiences has resulted in a concept of modernity that seems to be at variance with the conventional meaning of the term. Conventionally, Western history is divided into periods with a formal incision around 1500, the later period being the modern phase of Western society. If, however, modernity is defined as the growth of gnosticism, beginning perhaps as early as the ninth century, it becomes a process within Western society extending deeply into its medieval period. Hence, the conception of a succession of phases would have to be replaced by that of a continuous evolution in which modern gnosticism rises victoriously to predminnce over a civilizational tradition deriving from the Mediterranean discoveries of anthropological and soteriological truth. This new conception in itself does no more than reflect the present state of empirical historiography and, therefore, is not in need of further justification. Nevertheless, there remains the question whether the conventional periodization has no bearing at all on the issue of gnosticism; for it would be surprising, indeed, if a symbol that has gained such wide acceptance in the self-interpretation of Western society were not in some way connected with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of representation of truth.
从这一段看来,我更喜欢段译。the conception of a succession of phases,译为**“前后相继的分期概念”**,显然比“连续性阶段”要更容易理解;the fundamental problem of representation of truth,连续的属格短语,译为“对真理的代表这个根本问题”,也好过孙译的“真理代表的基本问题”——后者很不容易看出属格名词是作为宾格还是主格在使用。
至于“ it becomes a process within Western society extending deeply into its medieval period”,我是两种译本都不太喜欢,无论“现代性就是西方社会内部的一个过程,深深地渗透进了中世纪时期”,还是“那么它就变成了西方社会内部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深入延伸到了中世纪时期”,我都觉得不太好。至于a civilizational tradition deriving from the Mediterranean discoveries of anthropological and soteriological truth,翻译为“一个源于地中海世界对人类学真理和救赎论真理的发现的文明”,或者翻译为进而取得了对“一个源自地中海地区,发现了人论和救赎论真理的文明传统”的支配地位,我觉得前者属于“笨译”,后者可以归入难解的误译——反正我是看不懂。
但文本本身是极为重要的,有两个译本对照,对于学习研究而言意义重大。事实上,两个译本都可以说翻译得甚好——远远好过出版社给出的千字100元水准。这样好的译者,按照希伯来书11章的说法,是这个文化所不配有的。
去年翻译了一本关于威敏认信的历史神学书籍,因为涉及非常多的16-17世纪引文,翻译的时候很头痛,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这书采用了创新的翻译模式,没有从出版社拿翻译费,而是通过其他渠道得到资助。甚至出版此书的想法也是后来才出现的,本意只是作为一本参考教材而已。
从这个意义上看,此书的出版不仅可以让更多读者受益,也能帮助出版此书的机构。但即使是这样,最近有朋友告诉我,有出版界的朋友认为我翻译这样的书还是“狮子大开口”了,原话叫做“真敢要钱”——虽然我要的钱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看起来,这种对于译者价值的分歧将会长期存在下去,或许我们不必翻译什么书籍,只要出版几个书评杂志,比如“读书”或“上海书评”“四季书评”即可。而我早已和主流出版界绝缘。
暂时不说了,还有20万字的“领导力”教材要校对,这就闭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