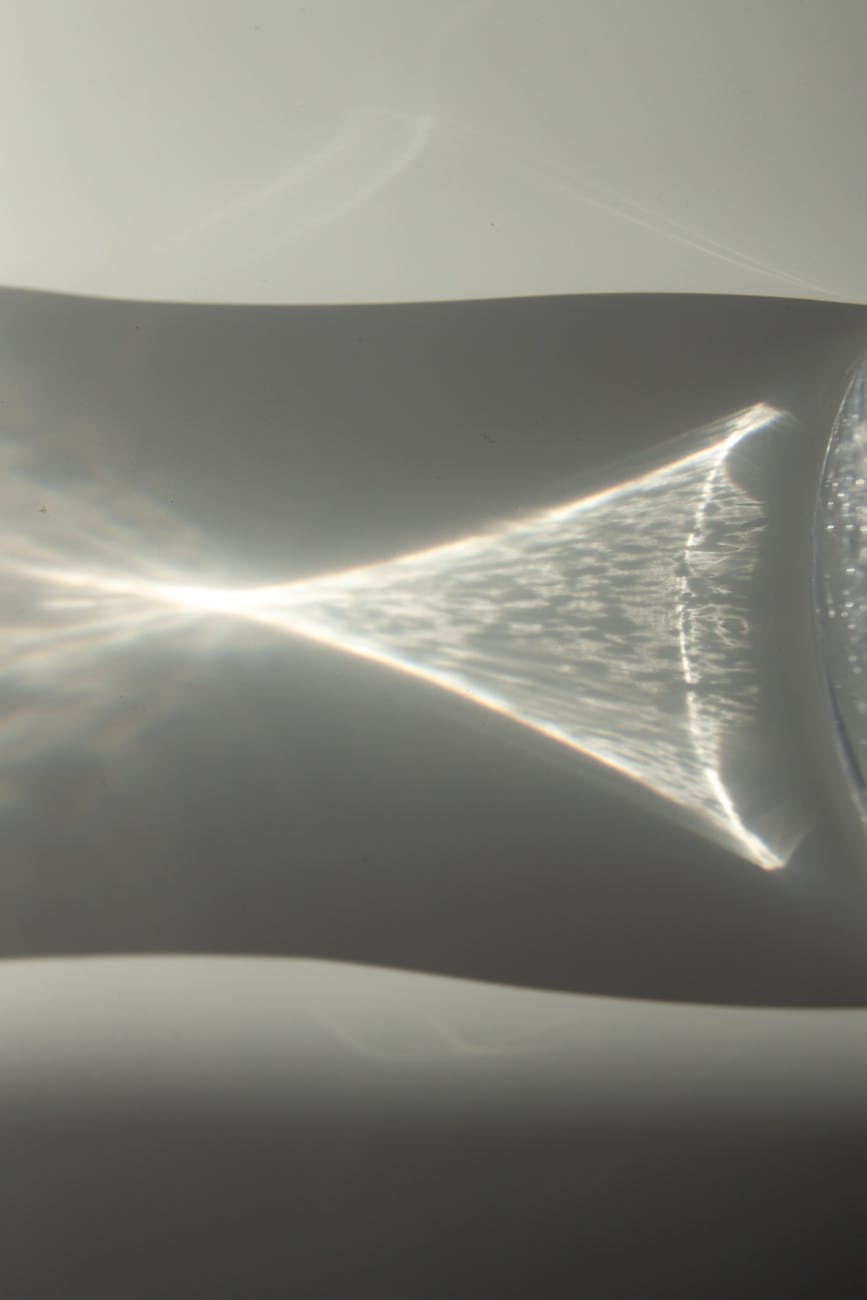主日崇拜结束之后,又和一位法学博士与一位北大读书放假回家的年轻人聊了若干“双盲”问题。
后来我发现,两位都是初来教会访问的新人,尽管我已经小心翼翼在讲道的时候不要引用太多神学术语,但他们还是提出了至少一个没有听说过的词汇——“植堂”。的确如此,没有人应当天生就明白“植堂”,特别是没有视觉效果,听我用舌头没卷到位的重庆普通话说这两个字,大约更是一头雾水。英语到是方便一些,我说“church planting”,顺便解释建立教会就像植树,栽下去就等着结果子。
我们又聊了若干其他话题,比如初来教会的人最感兴趣的大分类,“你们教会是天主教吗?你在负责一个教区吗?”诸如此类……不知道解释清楚没有。
今年规划了50次讲道。如果有限的两次出行外访也要讲道,基本上就齐活儿了。
即使如此,讲道前我也会紧张。
我的基本预备过程参见:事工哲学(68)|开发过程映射的讲道,即使不算太过于耗费时间,也算是相当耗费心力的过程。
每个世代留下的优秀传道人并不多,2000年以降,也不过金口约翰、司布真、坎贝尔摩根等百十来人而已。维基百科的“List of Christian preachers”一条,在清教徒传道人的小标题下,不过数人而已:
John Harvard (1607–1638)
Joseph Alleine (1634–1668)
John Davenport (1597–1670)
Matthew Henry (1662–1714)
Jonathan Edwards (1703–1758)
G. Campbell Morgan (1863–1945)
Martyn Lloyd-Jones (1899–1981)
是的,虽然许多人以为司布真是清教徒,但他和马丁路德金,以及葛培理等人,实在是浸信会教会的牧师。
照我看来,每个时代像我这样挣扎的传道人远远比留下精装大部头讲道集的传道人要多得多。
我有典型的传道人周一焦虑症和周末抑郁症。每到周一,就会开始为着即将到来的主日焦虑,每次礼拜之后,就会觉得已经用尽了所有的情绪能(emotional energy),连同身体真正的疲乏感。
中午聚餐的时候,我们也谈到一位我相信颇有实力的译者——从资历和教育背景上,以及他从前做过的一些事工上,我可以想象必定如此。但告诉我的朋友说,他显然志不在此,并没有将神学翻译视为一个事工。
这样的评论也容易理解。翻译,或者讲道,大概都是一样。讲道还算是在人前有些光荣的工作,而翻译几乎是一种自相矛盾——最好的译者是让读者直接见到原作者,意识不到翻译转换过程的译者。偶然潜心翻译一本20万字的经典,以为自己在神学翻译上的代表作,并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许多神学的PhD或者有功底的传道人或许都能做到;每天坚持翻译数千字,一年以平庸水准输出1百万字译文,坚持5年以上,或许是更难的事情。而每周日输出一篇好的讲道,坚持40年,大概是很少有人凭着自己的毅力和恩赐能成就的事情。
我仍然处于抑郁的状态。按照“压力管理”的原则,这是传道人的正常情绪发展曲线罢。讲道的时候投入了太多精力,太过于专注,肾上腺激素浓度调整得很高,讲道结束之后,需要一个平缓的释放和报复性抑郁的过程。对于我来说,或许周一是个合适的安息机会,所以这一次的释经讲道工作坊,我基本上没有什么动力来催促大家交作业,能装作精神饱满地样子,靠着4杯浓咖啡撑过两小时就算是胜利了。
但下一个主日仍然会来到。到了周二就必须打起精神来,开始预备和祷告。否则,没有预备好的焦虑感会以另一种方式慢慢地积累起来,到周五或周六的时候达到极限。
司布真是讲道前抑郁症,常常在书房里哭到崩溃,觉得自己上不了台;而我是讲道后抑郁症,蒙头一睡,或许自然就好了。好在Emma和孩子们都已经了解这种过程,于是周日下午都不太打扰我,允许我很好地睡一觉,在这样周复一周的起起伏伏之中,算是享受了主里面的平安。
2年前的另一次抑郁发作,参见“周末抑郁症”。
版权所有:Eddy Zhang
博客:https://eddyemma.com
出品人:跨文翻译(kuawentrans.com)跨文翻译以职场作为宣教平台。
 if you are ever moved to support this ministry or my family…
if you are ever moved to support this ministry or my family…
若您或您的教会愿意支持跨文翻译的事工,请使用以下二维码。